 BTC/HKD+0.68%
BTC/HKD+0.68% ETH/HKD+0.89%
ETH/HKD+0.89% LTC/HKD+0.4%
LTC/HKD+0.4% ADA/HKD+2.13%
ADA/HKD+2.13% SOL/HKD+4.27%
SOL/HKD+4.27% XRP/HKD+1.16%
XRP/HKD+1.16% 
汪曾祺
■
內容提要
青年汪曾祺以現代派詩為小說,把小說寫成晦澀的散文詩,他是一位詩人,還不是一個奧登意義上的小說家。是“自然”的都德、靜觀的阿左林和記流水賬的契訶夫叩響了汪曾祺這口鐘,讓他懂得要讓事事自己表現。讓事事自己表現,就意味著汪曾祺堅決撇開自己、學會做別人,他由此成為一位真正的小說家。也正是讓事事自己表現的決心和努力,讓他融通了中西文學資源,比如,他認定,歸有光就是“中國的契訶夫”。
■
關鍵詞
汪曾祺都德阿左林契訶夫
汪曾祺寫于1947年的《短篇小說的本質——在解鞋帶和刷牙的時候之四》,早已是文論經典。不過,很少有人注意到,此文存在一重頗富意味的斷裂。汪曾祺在文中回憶,1940年代初的西南聯大寫作課堂上,沈從文給學生出了一道題目,“一個理想的短篇小說”。彼時卞之琳所譯現代主義作品集《西窗集》正在風行,被其中的一些篇章弄到瘋魔的汪曾祺大聲說:“一個理想的短篇小說應當是像《亨利第三》與《軍旗手的愛與死》那樣的!”從脫口而出的現場到回憶的當下,五六年時間倏忽而過,他依舊認定它們就是短篇小說理想的樣子,態度卻有了不小的松動,作出如下的增補:
那兩篇東西所缺少的,也許是一點散文的美,散文的廣度,一點“大塊噫氣其名為風”的那種遇到什么都撫摸一下,隨時會留連片刻,參差荇菜,左右繚之,喜歡到亭邊小道上張張望望的,不衫不履,落帽風前,振衣高崗的氣派,缺少點開頭我要求的一點隨意說話的自然。
說它們好,是因為它們是小說,卻更像詩、像戲,契合他的寧可短篇小說像詩、像戲、像散文,就是不能太像小說的文體互滲觀;說它們還不夠好,則是因為它們一點都不像散文,而像散文可能才是理想的短篇小說的核心特征。他沒有意識到的是,像詩、像戲,就一定不像他所喜歡的不衫不履、瀟瀟灑灑的散文,它們壓根不兼容。從這個意義上說,增補不是意義的深化、延長,而是修正、顛覆。有趣的是,增補的大意和修辭,都來自周作人為廢名《莫須有先生傳》所作序言。這一有意無意的追慕、模仿表明,汪曾祺把理想的短篇小說等同于散文化短篇小說,并進一步把散文化短篇小說的美學風格徑直落實為周作人、廢名一脈的京派風——他的審美取向與《亨利第三》《軍旗手的愛與死》漸行漸遠,這是一場未免有些匆促的告別。
正是這一匆促的告別揭示出一樁事實:汪曾祺對于外國文學的接受是復雜的、流變的,他沉潛,又擺脫,總是在尋找更像自己、讓自己更是自己的對象。本文想要弄清楚的是:汪曾祺究竟受過哪些外國作家的影響,哪些人的影響被他擺脫,哪些人則讓他終身受益或是受限,這些擺脫、沉潛又折射出汪曾祺一個什么樣的自己來?
一“你將死于晦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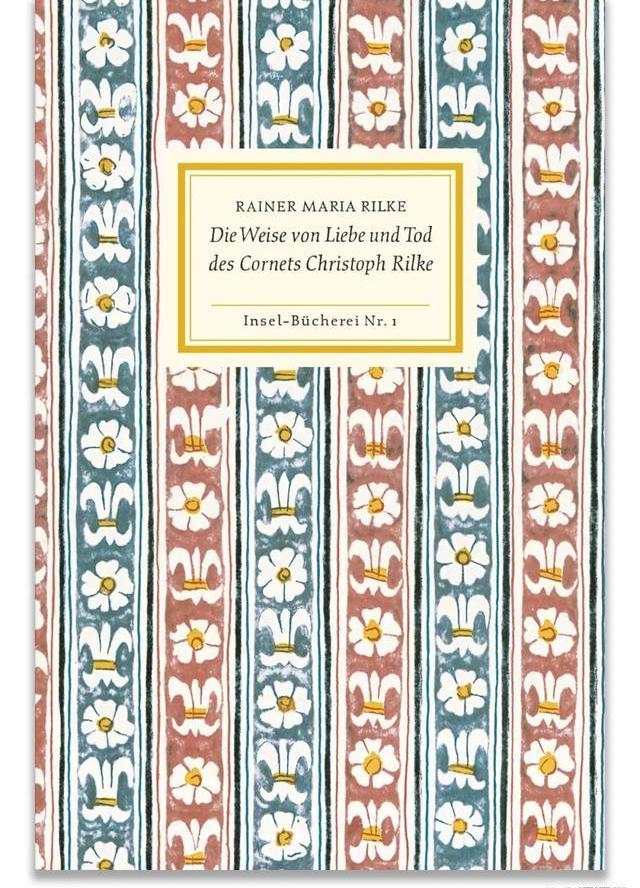
里爾克:《軍旗手的愛與死之歌》
1944年4月,戰時昆明,汪曾祺致書友人,說他看到溝邊躺著一個奄奄一息的士兵,連叮在身上的蒼蠅都趕不走了,眼睛卻還在看,又大又白。他接著說,“我記得這種眼睛,這也是世界上一種眼睛”,這雙眼睛讓他想起奧登寫死尸之眼的詩句:“有些東西映在里面,決非天空。”1993年6月,他又提到這個半世紀前猛然遭逢的“刺點”一樣的場景,并把誤記到奧登頭上的句子還給里爾克,還引用了奧登寫死尸的另一名句:他就要死了,就要“離開身上的虱子和他的將軍”了。里爾克的句子出自《軍旗手的愛與死》。明明認定《軍旗手的愛與死》是理想的短篇小說,卻說其中最有名的句子是詩句,還把它的作者給張冠李戴了,汪曾祺的錯誤讓人多少有些摸不著頭腦。不過,如果想到用奧登的詩句來表達他當時的“震驚”也許同樣貼切,因為里爾克說的是一個被殘殺的匈牙利農夫,奧登寫的是一位在中國戰場上死去的戰士,他們都在無情的戰爭中淪為肥料,不會再被記起,那么,我也許有理由不把這個錯誤看作是單純的過失,而是當成弗洛伊德意義上的有意味的“筆誤”。對此“筆誤”,我的解讀是:1.青年汪曾祺熱愛詩,本質上是一位詩人。他讀詩、談詩、寫詩,喜歡精彩的句子,一些看熟了的相似的句子在腦子里打架,再正常不過了,何況里爾克與奧登的句子都是出自當時任教于西南聯大的卞之琳的譯筆。2.本質上是詩人,他就認定最好的藝術樣式只能是詩,小說如果也有可取之處的話,只在于它的詩意或者詩化,而詩化小說就是一種獨特的詩。這一點,他在上面那封信里說得非常明了:“我向日雖寫小說,但大半只是一種詩,我或借故事表現一種看法,或僅制造一種空氣。”一個作為詩人的小說家的小說作法,大概就是以詩為小說。需要說明的是,被西南聯大時風所浸溉,汪曾祺著迷的是西方現代派詩,以詩為小說,也就是以現代派詩為小說。既是以現代派詩為小說,他的小說必然呈現如下特點:
Stake黑客將126,444.44枚MATIC轉移到新地址:金色財經報道,MistTrack在社交媒體X(原推特)上稱,Polygon上的Stake黑客(0xf83...3dc)剛剛將126,444.44枚MATIC轉移到新地址(0x22b...63f)。[2023/9/7 13:23:34]
首先,寫小說的第一要義就是要尋找精彩的句子。《西窗集》收了洛庚·史密士《小品》,其中一篇題為“詞句”,史密士一上來就問:“世界上,究竟,還有什么慰藉像語文的慰藉和安慰呢?”接著,他又說,他只為這一終將到來的時刻而憂傷:“最完美的隱喻一定會忘掉在人類化為塵埃的一天。”現世如此蒼白,唯美好的詞句可堪回味,這一現代派詩學的命題,青年汪曾祺自然心領神會。他說:“每一個字是故事里算卦人的水晶球,每一個字范圍于無窮。”又說:“我簡直想把人生也籠括在幾個整整齊齊的排句里。”問題在于,小說不同于詩歌,小說中精彩的句子如果過分璀璨的話,就不可能也沒有必要與周邊的句子融成一體,它們就像是一些琳瑯滿目的補丁。比如,《小學校的鐘聲》說到小學上課,就是“我們像一個個音符走進譜子里去”;下課鐘一敲,則是大家一下子鼓噪起來,“像一簇花突然一齊開放了”。兩個比喻美則美矣,與整篇小說淡淡的意識流風卻是相捍格的。再如,1947年版《異秉》寫藥店一天的工作結束,“該蓋上的蓋了,該關好的關好”,這就夠了。不過,汪曾祺又用括號加上一個比喻:“鳥都棲定了,雁落在沙洲上。”鳥棲、雁落固然詩意,卻跟蓋上、關好的日常動作無涉。結束一天忙碌的人們在藥店大堂的燈下聚齊,照例開始胡侃,汪曾祺又忍不住用了一個險峻的比喻:“一齊渡過這個‘晚上’像上了一條船。”這個比喻引發的后果就是,讀者的注意力從這個晚上的人、事、氛圍轉移到了這個晚上、這條船本身,敘事人好像從高處俯瞰著這個晚上、這條船——讓青年汪曾祺感到愉悅的,也許就是這個俯瞰的姿勢以及俯瞰著的高高在上的自己。
其次,是晦澀。致力于尋找精彩的句子,青年汪曾祺當然迷戀比喻,因為比喻是讓本體與喻體相互映照從而獲得新奇的美感,并讓意義增生、游移、混雜起來的方法。1943年,他寫下一句話:“每一朵花都是兩朵,一朵是花;一朵,作為比喻。”他的意思是,比喻跟真實一樣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話。1945年,他寫了一首題為“春天”的詩,結尾是:“看人放風箏放也放不上,獨自玩弄著比喻和牙疼。”這兩句詩說明,對于他,比喻跟牙疼一樣,都是忘不掉、擺脫不了的深入骨髓的東西,因而也就是只能“獨自玩弄”的私密、切身的東西。越是私密、切身的東西,對于別人來說,當然就越是一個謎,晦澀、不可解。就這樣,青年汪曾祺寫下一批精彩但讓人有些不知所云的句子。比如,《誰是錯的》用一個比喻來為一段行動和心理作結:“我的心,似乎有個小小抽象的錨拋在抽象的石灘邊,泊定了。”泊定,大概是終于穩妥了的意思,但抽象的錨與抽象的石灘又是什么?我的看法是,這個句子并不是在描述現實生活中某一可能發生的場景,而是受到另一個句子觸發從而衍生出來的,這個源句子就是《軍旗手的愛與死》有關女人手勢的一個比喻:“你簡直要說她們是在你攀不到的高處采摘你看不見的姣好的玫瑰花。”由一個迷離恍惚的句子生出的另一個迷離恍惚的句子,怎么求得出甚解?其實,艾略特、奧登這些“新的奇異的神明”的詩大抵是晦澀的,追慕這樣一種詩風,青年汪曾祺的小說能不晦澀?
再次,則是把小說寫成了散文詩。詩,是一種把自己寫出來的文體,以詩為小說,也就意味著小說家寫小說的沖動和目的就在于寫出他自己。這一點,青年汪曾祺談得很多、很直白。他說:“一切為了述說自己,一切都是述說自己,水,神,你說了些甚么?”又說:“我的小說里沒有人物,因為我的人物只是工具……如果我的人物也有性格,那是偶然的事。而這些性格也多半是從我自己身上抄去的。”不過,現代派詩人反對把自己直接寫出來,認為這樣的詩往往流于說教和感傷,不足以說服和感動讀者。艾略特就說:“詩不是放縱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現個性,而是逃避個性。”受艾略特“非個性化”主張的啟發,袁可嘉提出“新詩戲劇化”方案:“即是設法使意志與情感都得著戲劇的表現,而閃避說教或感傷的惡劣傾向。”“新詩戲劇化”的首位原則是表現上的客觀性與間接性,直接的文本呈現形式就是第三人稱普遍取代第一人稱。以詩為小說的美學取向與“新詩戲劇化”的要求相暗合:小說的文體特征讓汪曾祺很難直抒胸臆,他必須從“我”的身上離析出一個“他”,用“他”來表達“我”,比如《序雨》里的“他”;或者以“我”來觀“他”,“他”比“我”更是“我”,一個因為抽離因而更能接近“我”的“我”,比如《匹夫》中的西門魚與荀、《綠貓》中的“我”與栢。這樣一來,不管是用“他”表達“我”,還是以“我”觀“他”,都是汪曾祺自己在沉思,他寫的是小說,其實更像是散文詩——把自己寫出來,這是詩;非韻文、第三人稱,這是散文;雜糅起來,這就是散文詩。
香港約有10家基金經理基金經理已獲得第9類(資產管理)牌照:金色財經報道,德杰律師事務所合伙人 Michael Wong 表示,自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SFC) 于 2019 年發布指引以來,香港有 10 家基金經理升級了管理加密貨幣的牌照。有了必要的第9類(資產管理)牌照,基金經理將能夠將其管理總資產價值的 10% 投向數字資產領域。[2023/4/28 14:33:30]

苦艾酒
說起散文詩,當然要說到波德萊爾,是波德萊爾最早設想、呼喚散文詩這一奇異文體的。青年汪曾祺熟讀波德萊爾。《匹夫》說到一位“吞食波特萊爾”的友人,平地突起一個比喻:“波特萊爾,一頭披著黑毛的獅子。”到了晚年,他還記得,讀大學時,“波特萊爾的《惡之花》《巴黎之煩惱》是一些人的袋中書——這兩本書的開本都比較小”。對波德萊爾揣摩既久、已熟,他自然而然把小說寫成《巴黎的憂郁》一樣晦澀的散文詩。波德萊爾對于青年汪曾祺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1.意象的借用。《春天》中,王大爹對小孩子們說:“你們呆在這兒干甚么呢?看著貓兒的眼睛,該有兩點多鐘了吧,去放風箏罷……”讀者難免納悶:為什么要從貓的眼睛看時間?看得出來嗎?其實,這句有些無厘頭的話來自《巴黎的憂郁》里的《時鐘》:“中國人從貓眼里看時辰。”不過,汪曾祺的借用不僅忽略了波德萊爾的前后文,《春天》的田園風與“貓眼”所傳遞出來的現代的憂郁、煩悶也不協調。2.框架、立意的沿襲。汪曾祺自己最滿意的小說是《職業》。1947年版《職業》這樣分析小孩平日里叫賣“椒鹽餅子西洋糕”的聲音:“你可以聽得出一點嘲諷,委屈,疲倦,或者還有寂寞,種種說不清,混在一起的東西。”有一天,小孩休息,從“職業”中解放出來,于是,“你從他身上看出一個假期,一個自在之身”。只有一具“自在之身”才能返身直面自己從來都是被捆縛的身體,并戲謔性地來上一句“捏著鼻——子吹洋號”。這種從卑微、沉重、日復一日的勞作中掙脫而出的輕倩、靈動的“自在之身”,波德萊爾《寡婦》早有動人描述:一個迷人的秋天的下午,一位悲哀、孤獨、僵直的老婦坐在公園的偏僻角落,遠離人群,入神傾聽遠方的音樂會,“這大概是這位純潔的老人的唯一的小小放蕩吧,是從沒有朋友、沒有聊天、沒有歡樂、沒有知心人的沉重的日子里獲得的安慰吧……”1982年版《職業》略去那些波德萊爾式機智、迷離的議論,讓立意含藏起來,但立意本身還是一以貫之的。3.趣味的感染。《綠貓》中的栢在寫一篇同名小說,說的是一個喜歡畫畫的孩子,畫了一只綠貓,被老師打了手心,后來他做公務員,不得意,還想畫畫,畫不成,再后來他老了,有人送他一只貓,他把貓染成綠色,沒有兩天,他死了。這里的問題是,這個郁郁而終的人為什么要畫世界上并不存在的綠貓,他所認定的最迷人的貓為什么必須是綠色的?要回答這個問題,也必須回到波德萊爾:綠色是苦艾酒的顏色。波德萊爾《藥》就是一首“苦艾酒頌”:“這一切都不如你碧綠的眸子/流出的,你的眼睛/是湖水,倒映出我戰栗的心靈……”《月亮的恩惠》中,情人的眸子是綠的,大海也涌動著無邊的、綠色的波濤。王爾德對比亞茲萊說:“我一把你的畫放在面前,就想喝苦艾酒,它像陽光下的碧玉一樣變換色彩,迷惑感官。”我想,不必多舉例,就已經可以認定,綠貓是一只現代派的貓。
不過,青年汪曾祺很快就對自己的現代派趣味產生動搖、疏離。1944年5月,他在信中說:“我的小說一般人不易懂,我要寫點通俗文章。”寫于同年的《葡萄上的輕粉》說,“沉默也是一種語言”,還說,“文到全篇都是警句時便不復有警句”,更對自己的寫作作出直截了當的宣判:“你將死于晦澀!”那么,汪曾祺將如何離開晦澀,離開現代派,他又是從哪些外國作家那里獲得離開的動力和資源的?
二詩人,還是小說家?
除了波德萊爾、里爾克、奧登等詩人,還有一些外國小說家、散文家也影響了青年汪曾祺,讓他差點“死于晦澀”。比如,汪曾祺一再談到伍爾芙的意識流對他的影響。在“小傳”中,他說:“大學時期受阿左林及茀金尼沃爾芙的影響,文字飄逸。”“飄逸”說的不只是靈動、瀟灑,更是指向意識的跳躍、飄忽,讓人墮云霧中。最伍爾芙的汪曾祺作品是1948年版《道具樹》。這是汪曾祺對于舞臺的一通遐思,一縷縷思如白云一般舒卷、折疊、纏繞,之間卻無邏輯關聯,更不會通往一個關于舞臺的終極之思——終極之思讓作為過程的思得以明晰。1992年,汪曾祺重寫《道具樹》,重寫版有一個有意味的增補:“我躺在道具樹下面看書,看弗吉尼亞·伍爾芙的《果園里》。”要知道,《果園里》就是以米蘭達躺在蘋果樹下看書開頭的,于是,這一增補再清楚不過地說明,汪曾祺的舞臺就像伍爾芙的果園,舞臺上、果園里都是一些不可解的意識流在涌動。
去中心化衍生品交易協議Veax完成120萬美元pre-seed輪融資:11月17日消息,基于 NEAR 的去中心化衍生品交易協議 Veax 宣布完成 120 萬美元 pre-seed 輪融資,Circle Ventures、Proximity Labs 、 Outlier Ventures、Tacans Labs、Qredo、Skynet Trading、Seier Capital 和 Widjaja Family 等參投。據悉,其顧問委員會包括 Skype 前首席運營官、 Concordium Blockchain 創始人等。[2022/11/17 13:18: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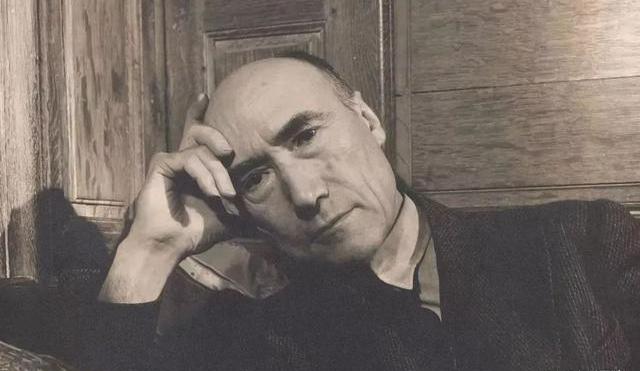
紀德
更重要的,當然是紀德。紀德是彼時大學生追慕的偶像,青年汪曾祺未能免俗,成天夾著一本紀德泡茶館,還一再地贊紀德、引紀德、學紀德。他說,“紀德的書總是那么多骨。我忘不了他的像”;也說,“我對紀德的話一向沒有表示過反對”;還說,“紀德發現剛果有一種土人,他們的語言里沒有相當于‘為甚么’的字”;晚年回想自己的昆明游蹤,又說,“晚上,寫作,記錄一些印象、感覺、思緒,片片段段,近似A.紀德的《地糧》”。《綠貓》就是一篇向紀德致敬的作品。跟紀德的《帕呂德》《偽幣制造者》一樣,《綠貓》也是在說主人公想要寫作一部擬想中的同名小說,因此對人大談特談小說寫法、人生感悟,最終竟為源作者敷衍出一篇小說來。有趣的是,這些小說中的小說無一例外地難產,也許,太了然于小說作法反而讓他們喪失了去寫一篇小說的能力。他還要把紀德的書寫進自己的書,以此建立一種更本質、恒久的關聯。比如,《牙疼》里的梁醫生就是一個紀德迷,他的候診室放著一本紀德。
那么,對于青年汪曾祺,紀德究竟有何魔力?紀德是“瞬間的情人”,決不專一,渴望變化,聽從欲望的引領,與沿途相逢的每一個美好的人、事交融,就像他筆下的忒修斯:“見到潘神、宙斯或忒提斯向我展示的一切美妙的東西,我都會勃起。”也就是說,絕對的變才是紀德恒定的不變,他總是與昨天的自己迅速、決然地斷裂,從而獲得自身的連續性、統一性,他的“我”這才是確立的、牢靠的。這一變才不變的辯證法,被《偽幣制造者》里的愛德華明明白白寫在日記里:“我永遠只是我自以為我是的那個人——而他又不斷地在變,因此我如果不從旁守護著,早上的我就已不認識晚上的我。沒有再比我和我更不同的。”變才不變的紀德是浪子,是惡魔,是饕餮,他有如此龐大、激蕩的能量需要吞吐,最上手的敘述方法就一定是像《人間食糧》那樣,虛擬出一位傾聽者、受教者納塔納埃爾,然后向他滔滔不絕地說起那些再不說就會把自己脹破、沖垮的生命箴言。不多的時候,青年汪曾祺也是紀德一樣的浪子,他說:“精美的食物本身就是欲望。濃厚的酒,深沉的顏色。我要用重重的杯子喝……我渴望更豐腴的東西,香的,甜的,肉感的。”畢竟不可能擁有紀德一樣奔騰不息的能量,用汪曾祺的話說,就是“我夢想強烈的愛,強烈的死,因為這正是我不能的,世界上少有的”,于是,他所能學的,就只是紀德那種一再地說、不停地說,把“我”說出來并因而成為“我”的言說的姿態和方式。這樣一來,青年汪曾祺寫作的動力和旨歸,就是對著虛空中的納塔納埃爾說出屬于自己的寓言、重言,更多時候則是卮言,這些說出來的篇什都是汪曾祺之“我”的直接表達,它們不管是散文詩還是散文詩一樣的小說,其實都是汪曾祺的抒情詩,就像《人間食糧》就是紀德的抒情詩一樣。
不過,紀德不是一直在變?何況王爾德早已警告紀德,執著于“我”大錯特錯:“Dear,答應我:從今以后切勿再用‘我’字……在藝術中,您看,是不許有第一人稱的。”詩興遄飛中的栢忽然想到一句紀德的箴言:“若是沒有,放它進去!”栢及其身后的汪曾祺的意思是,擁有“最豐富的生活”的“我”是精美、純粹、劇烈的,“我”就是詩,世界太粗陋、蒼白,哪有什么詩,那么,來,讓“我”把“我”的詩放進去。這句話出自卞之琳所譯《新的食糧》:“投向未來吧。詩,別再傳寫在夢里;想法在現實里找到它。如果它還不在那里,放它在那里。”夢,是一個人的詩,就像栢的苦吟;把詩寫向未來,把未來寫成詩,則是打破“我”的拘禁,讓“我”抵達并消融于萬匯,“我”將在萬匯的喧響中聽到自己隱約的心跳。原來,紀德正在竭力掙脫出他的“我”,這是他又一次的斷裂,最新的律令。對此,《新的食糧》另有更明確的宣告:“真正的雄辯放棄雄辯;個人惟有在忘卻自己的時候才肯定自己……基督是在放棄自己的神性的時候才真正變成了神。”跳出“我”、走向萬匯的紀德不再是抒情詩人,而是小說家,因為小說家就是要“貼”著別人寫的。詩人與小說家的不同,奧登《小說家》也有精彩描述:詩人像風暴,像輕騎兵,可是小說家“必須掙脫出少年氣盛的才分/而學會樸實和笨拙,學會做大家/都以為全然不值得一顧的一種人”。如果說做小說家就意味著收起“我”,學會去做一個也許跟“我”毫無關聯的別人的話,那么,卞之琳認定“社會主義者與小說家簡直沒有多大分別”,從而得出紀德實現了社會主義轉向的結論,也就是水到渠成的。可惜的是,汪曾祺并沒有領會紀德這一根本性的斷裂,他忘不了的是一個早已成為蟬蛻,癡迷于書寫“我”之“內在的景致”的紀德,正是在這一個紀德的嗾使之下,他宣稱要朝世界放進他的詩——他離紀德、奧登、卞之琳所理解的小說家還很遠,他該如何實現自己的小說家轉向?
DOGE的前50名持有者共持有871億枚DOGE,占總供應量的63.71%:11月1日消息,據Lookonchain統計數據,DOGE的前50名持有者共持有871億枚DOGE(約126億美元),占總供應量的63.71%。與一周前相比,他們的持有量減少了7.61億枚DOGE(1.1億美元),與昨天相比,他們的持有量增加了4.84億枚DOGE(7000萬美元)。在過去一周內,有12個地址增持了DOGE,7個地址減持了DOGE,15個地址在過去6個月內沒有交易DOGE。[2022/11/1 12:04:53]
1947年,寫作《綠貓》的前一個月,汪曾祺寫出《落魄》。《落魄》寫的是一個在昆明開小館子的揚州人的“落魄”史:一開始,他炒菜時穿一身鐵機紡綢褲褂,頭發梳得一絲不亂,除了流利合拍的翻炒手法,“無處像個大師傅”;落魄后,臉變得浮腫,是暗淡的癡黃色,一件黑滋滋的汗衫,衣褲上全是跳蚤的血點子。對于這個倒霉且順從于自己的霉運的揚州人,“我”只有厭惡:“我恨他,雖然沒有理由。”不過,千萬不要被厭惡牽著鼻子走,因為“我”之前的歡喜是如此強烈,哪能被后來的厭惡一筆勾銷?比如,揚州人新討了女人,他不時走過去跟她低聲說上兩句,或者伸手拈掉她頭上的草屑,“我”看在眼里,覺得“他那個手勢就比一首情詩還值得一看”。汪曾祺的真實用意在于,讓歡喜與厭惡之間形成一種古怪的張力:當時有多歡喜,如今就有多厭惡,而厭惡又讓記憶中的喪失了的歡喜越發顯得美好,讓人覺得疼惜。歡喜與厭惡彼此映照的主題,也許有一點現實的依據,文學淵源卻一定是都德《磨坊文札》里的《兩家旅店》。《兩家旅店》說的是兩家相鄰的旅店,一家擠滿了騾馬和車輛,叫喊聲、酒杯碰撞聲、臺球滾動聲響成一片,一家卻門可羅雀,大門口長出了青草。后者的老板娘是一個病懨懨的婦人,她用一種心不在焉、無動于衷的語氣告訴“我”,她的店也曾興盛過,自從那個阿萊城的漂亮、風騷女人在對面開店后,人全跑過去了,連她的丈夫都成天廝混在那里,圍著那個女人縱情歌唱。是太鐘愛這個主題了吧,1985年,汪曾祺又寫出一篇中國版《兩家旅店》,《故人往事·如意樓和得意樓》:滿面紅光、精干、勤勉的胡二老板和他的熱氣蒸騰的如意樓就是阿萊城的女人和她的旅店,沒精打采、目光呆滯的吳老二和他的用不了多久就要關張的得意樓就是那個病懨懨的女人和她的旅店。值得注意的是,小說結尾一語挑破這一比照所要說明的道理:“一個人要興旺發達,得有那么一點精氣神。”用這個道理來闡釋引而未發的《落魄》和《兩家旅店》,同樣順暢、妥帖,而順暢、妥帖反過來又證明了三篇小說的同構性。有“精氣神”的生命真是令人歡喜。到了1993年,汪曾祺還記得半個世紀以前昆明映時春的一個堂倌,手、腳、嘴、眼一刻不停,麻溜之至,清楚之極。他不由得感嘆:“看到一個精力旺盛的人,是叫人高興的。”
從《落魄》追溯到《兩家旅店》,并非在強行比附,而是有著扎實的學理依據的:1.《磨坊文札》中文全譯本早在1927年就已推出,影響了沈從文、師陀等一眾作家,汪曾祺對它當然不會陌生。2.汪曾祺喜歡都德,他說:“我不喜歡莫泊桑,因為他做作,是個‘職業小說家’。我喜歡都德,因為他自然。”《徙》中的高北溟先生教國文課,教材自編,選了白居易、歸有光、鄭板橋,外國作品,只有一個《磨坊文札》。這是一份虛擬選本,而選本正是文學批評的一種重要樣式。這份選本揭示出如下信息:首先,《磨坊文札》與歸有光們的作品一樣,都是“有感慨,有性情,平易自然”的;其次,在歸有光們的作品的熏陶下,少年汪曾祺喜歡“自然”,這一審美取向后來被西方現代派的晦澀風所壓抑,再接著又被“自然”的《磨坊文札》喚醒,《落魄》就是一個明證——除了有一個太有“精氣神”的紀德一樣的“我”在或歡喜或厭惡地凝視著揚州人,《落魄》就是在極“自然”地書寫著一個人的起落,就像《磨坊文札》,也像歸有光們的作品。更重要的是,汪曾祺跟這個揚州人并無淵源,他開始盡可能地收起他的“我”,試圖去認識一個“大家都以為全然不值得一顧”的人。從這個角度說,寫作《落魄》的汪曾祺還是詩人,同時又開始了奧登意義上的小說家轉型,助推他開啟這一轉型的精神資源之一,就是“自然”的都德和他的《磨坊文札》。《磨坊文札》對汪曾祺的影響持續、深遠。寫出《如意樓和得意樓》未久,他又寫作《橋邊小說三篇·茶干》。《茶干》結尾說,一個人監制的食品成為一個地方的代表性特產,真不容易,“不過,這種東西沒有了,也就沒有了”。《高尼勒師傅的秘密》中的磨坊給這個地方帶來過繁榮和歡樂,就像膾炙人口的連萬順茶干一樣。如今,風力磨坊就要消亡,都德的態度同樣是豁達的:“在這個世界上,什么事都有完蛋的日子”,磨坊、駁船、御前會議,都一去不復返了。
鏈上分析師:交易所庫存BTC達到近三年的最低值:金色財經消息,鏈上分析師Phyrex發推表示,從交易所的存量數據來看,經過今天大幅的減持后,交易所的庫存BTC又一次迎來了近三年的最低值,雖然這并不直接影響到BTC的價格,但是體現出了較強的購買力。[2022/7/7 1:56:54]
三“我要事事自己表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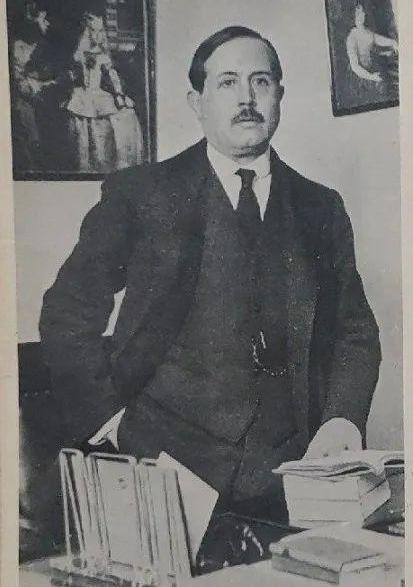
阿左林
汪曾祺說得最多且經常一并列舉的外國作家是契訶夫、阿左林,而且,越到晚境,說得越頻繁,認同越深,他在他們身上更本質地找到自己、回到自己,他說的是他們,其實是在勾畫自己理想的樣子。比如,他說,“我是很喜歡契訶夫和阿左林的作品的”,又說,“外國作家里我最喜歡的是:契訶夫和一個西班牙作家阿索林”。
1930年,戴望舒、徐霞村合譯的《西萬提斯的未婚妻》出版,阿左林開始為中國讀者所接受。1936年的《西窗集》收了一些阿左林小品,1943年,卞之琳又翻譯出版《阿左林小集》,大大推動了阿左林在中國的傳播。作為卞之琳譯作的忠實讀者的汪曾祺當然不會錯過阿左林。他說,大二以后,受阿左林的影響,“寫了一些很輕淡的小品文”。到了晚年,他更鄭重其事地說:“阿索林是我終身膜拜的作家。”他經常把阿左林對自己的影響,錯誤地歸結為一種“明澈的、覆蓋著清涼的陰影”的意識流,并因此把阿左林和伍爾芙歸攏在一起。只有在不必用意識流來突顯自己的新與現代的時候,他才能一語道出阿左林的魅力所在:“他對于世界的靜觀態度和用寫散文的方法寫小說,對我有很大影響。”對于這句話,我的理解是:1.現世如此擾攘,唯童年往事一片澄明,能夠打開這片澄明之境的,只能是一個靜觀的人。阿左林就是靜觀的。他的《小哲學家自白》追憶自己在一座陰沉、暗淡的小城度過的童年,并用經常聽到的三句話——“多晚了!”“我們可以干什么呢?”“現在他就要死了!”——來總結西班牙人的民族心理:聽天由命、悲哀、逆來順受、令人寒心的死感。就是這份追憶童年往事時的靜觀,讓卞之琳不禁感喟:“Senor阿左林,這些小品可不是只合在燭影下譯嗎?”也正是這份靜觀影響了汪曾祺,讓他回到童年、回到故鄉,去書寫那些輕甜、微苦的“故人往事”。在燭影下譯阿左林的卞之琳聽著窗外“硬面餑餑”的叫賣聲,想起周作人在介紹《一歲貨聲》的文章里說到過這種聲音。耐人尋味的是,他在“豈明先生”前面加了一個古怪的定語——“前幾年在《駱駝草》上談到‘西班牙的城’的”。他的用意在于,在阿左林與周作人、《駱駝草》等京派的人、事、物之間建立一種本質的關聯。一個合理的推測是:阿左林也許就是汪曾祺走向周作人、廢名的中介,或者說,汪曾祺在他們身上看到了家族相似性。2.靜觀意味著“我”的后撤,以及對于他和他們的絕不驚擾的“看”,就在這樣的“看”的過程中,他和他們一直以來隱而不彰的本來面目終于得以浮現。對于這種“看”,阿左林有過動人描述:“這些皮匠的緩慢、有規律的動作。獨一無二的瞬間。另一個動深情的瞬間。這些匠人沉默的、平靜的工作在鮮明的日光中,詩人則工作、沉思在上邊,在窗后。”阿左林的“看”給汪曾祺帶來兩重影響。首先,“看”到的他和他們的生活一定是日常的,因而也是瑣屑的、前形式的、未經闡釋的,呈現這樣的生活的合適形式,就是散文或者散文化的小說——阿左林和汪曾祺的很多作品究竟是散文還是小說,端賴他們自己認定。其次,能從其中“看”到“獨一無二的瞬間”的對象肯定不是農民,因為勞作中的農民是重復的、消耗的、疲憊的,就像梵高的傷痕累累的“鞋”;一般情況下多是手藝人,就像阿左林的皮匠、金匠,因為手藝人有熟極而流的瀟灑,更有人與對象交融到一處的渾然與自由。后來的汪曾祺一“看”再“看”、一寫再寫的都是賣熏燒的、做炮仗的、車匠、錫匠、銀匠之類的手藝人,大概跟年輕時看熟了的阿左林脫不了干系。
比《落魄》還要早兩年,汪曾祺寫作《老魯》。《老魯》快結束時沒頭沒腦地引了一句契訶夫:“阿——契訶夫主張每一篇小說都該把開頭與結尾砍去,有道理!”據布寧回憶,契訶夫之所以主張刪除開頭、結尾,是因為“在這類地方,我們小說家最容易說假話”。有趣的是,伍爾芙說,契訶夫小說最初給她的印象并不是質樸,而是迷亂,因為它們概無主旨。而它們之所以沒有主旨,是因為契訶夫決不給它們一個明確的結尾,以至于讀者“有跑過了信號之感,要不然就好像一支曲子沒有預期的和音而突然終止”。其實,人生只有一個結尾,那就是終將到來的一死。本雅明說,死亡賦予死者的一生巨細以一種權威,“這權威就是故事的最終源頭”。他的意思是說,是死亡讓生命獲得完整性,作為一個整體的生命就是一個故事,而故事總是通往一個主旨、寓意,或者叫“啟迪”的。只要死亡還沒有降臨,你就處于生命的局部,你的生命就還沒有獲得自己的形式,就是松散的、瑣碎的,你還不是故事,你還沒有自己的主旨。不過,一般情況下,小說都會有一個精心設置的結尾,這樣的結尾可能就是僭越,是“說假話”,是以“假死”的方式強行賦予松散、瑣碎的生命以整體性,并從中歸結出一個虛假的主旨——這個主旨跟對象無關,屬于講故事的人。當汪曾祺意識到,必須像契訶夫一樣砍去開頭、結尾時,他就已經認識到應該力避“我”對于對象的僭越,讓對象以自身的樣子呈現出來。
堅決克制住“我”,還對象以本身的樣子,這就是契訶夫給予汪曾祺的重要啟示。契訶夫在給哥哥的信中說:“只要老實一點就行了:完全撇開自己,不要把自己硬塞到小說的主人公身上去,哪怕只把自己丟開半個鐘頭也好。”正因為完全撇開了自己,契訶夫寫作時沒有自己的、宗教、哲學等方面的世界觀,只限于描寫人物“怎樣相愛,結婚,生孩子,死掉,以及他們怎么說話”,一句話,就是記錄他們的生活的流水賬。汪曾祺同樣撇開自己,嚴防自己的理念入侵對象。他說:“完全從理念出發,虛構出一個或幾個人物來,我還沒有這樣干過。”又說:“我最反對從一個概念出發,然后去編一個故事,去說明這概念,這本身是一種虛偽的態度。”沒有理念的賦形,生活就是一本流水賬。汪曾祺喜歡流水賬。他說,廢名《竹林的故事》就是幾個孩子的生活的“流水”,還用括號說明,舊時店鋪把逐日所記賬目稱作“流水”,“這是一個很好的詞匯”。像流水賬一樣流淌,就像是一棵樹在舒舒展展地生長,它不會事先想到如何長出枝葉,一枝一葉的生長卻又是有道理的、注定的,這樣的小說如果也有結構,那就是“隨便”。“隨便”就是周作人說廢名的“灌注瀠洄”和“披拂撫弄”,就是都德的“自然”,“隨便”的小說就是散文化小說。撇開自己、學會做別人的小說家不相信風景描寫,因為風景一般出自敘事人的凝視、賞玩,而風景中的人物只看到平淡無奇的日出日落。于是,契訶夫說:“風景描寫的鮮明和顯豁只有靠了樸素才能達到,像‘太陽落下去’‘天黑下來’‘雨下了’這類樸素的句子就是。”汪曾祺說過幾乎一模一樣的話,只是他也許已經不記得曾經讀過它的母本:“現代小說寫景,只要是:‘天黑下來了……’,‘霧很大……’,‘樹葉都落光了……’,就夠了。”他們也懷疑心理描寫,因為心理隱藏在“面孔”后面,是不可見之物,被離析出來的可見的心理一定出自敘事人的凝視、解剖,而解剖無異于殺死對象。于是,契訶夫說:“最好還是避免描寫人物的精神狀態:應當盡力使得人物的精神狀態能夠從他的行動中看明白。”汪曾祺的反問更是銳利:“人有甚么權利去挖掘人的心呢?人心是封閉的。那就讓它封閉著吧。”人心如果有所泄露的話,只能是在人物的行動和神態中,因為行動和神態是可見的。他們還一樣地喜歡追憶,喜歡往事,因為隔著一段距離之外的往事雖然未免有些變形,回憶者也會做出一些取舍,但它們被時間所淘洗、摩挲,它們更是它們自己,散發著真意的淡淡光輝。于是,契訶夫說:“我不能描寫當前我經歷的事。我得離印象遠一點才能描寫它。”而“復出”之后的汪曾祺一直在“文章淡淡憶兒時”。他們的區別只在于撇開自己的堅決的程度。契訶夫的寫作箴言是:“要到你覺得自己像冰一樣冰的時候才可以坐下來寫……”冰到殺死了“我”,也就喪失了抵達對象的可能,或者說對象的不可抵達才是對象唯一可知的真相。于是,契訶夫一再說,“這世界上沒有一件事情弄得明白”,美與丑、哀與樂、崇高與滑稽總是奇異地混雜在一起,這樣的世界讓他啼笑皆非。汪曾祺強調世道人心,一廂情愿地要給這個他大概也弄不太明白或者是不敢弄得太明白的世界送去“小溫”——他終究不忍把自己撇得太開、太清。不過,他倒是一眼看出沈從文跟契訶夫一樣冰:“什么都去看看,要在平平常常的生活里看到它的美,它的詩意,它的亞細亞式殘酷和愚昧。”
1947年,汪曾祺致信唐湜:“我缺少司湯達爾的敘事本領,缺少曹禺那樣的緊張的戲劇性。”這句話并不是對于自身不足的提示,而是在宣示自己日益成熟、穩定起來的看法:日常生活不存在驚心動魄的戲劇性,它毋寧是重復的、舒緩的、破碎的。不過,日常生活也有自己的辯證法:日常生活向前緩緩推進,今天不過是昨天的重復,裂口就在不知不覺中被撕開、扯大,以至于無法彌合。這才是最深沉、曖昧且本質的戲劇性。對于這樣的戲劇性,契訶夫亦有闡明:“人們吃飯,僅僅吃飯,可是在這時候他們的幸福形成了,或者他們的生活毀掉了。”正因為戲劇性的深沉、曖昧,汪曾祺需要叩一叩對象,就像叩響一口鐘:“我要事事自己表現,表現它里頭的意義,它的全體。事的表現得我去想法讓它表現,我先去叩叩它,叩一口鐘,讓它發出聲音。我覺得這才是客觀。”關于“叩鐘說”,唐湜如此解讀:“更貼近人生,更能傾聽人生,放棄同時也完成了自己……”所謂“放棄同時也完成了自己”,也就是撇開自己、學會做別人從而做一個奧登意義上的小說家。我還要把“叩鐘說”當作一個比喻,來說明外國文學對于汪曾祺的影響:波德萊爾、里爾克、艾略特、奧登、伍爾夫這些“西窗雨”頻頻敲打向汪曾祺這口鐘,只聽到悶悶的一點回聲;是契訶夫、阿左林、都德真正地叩響了他,他通過他們成了他自己,在時間的長風中鏗然作響。有趣的是,他還把歸有光稱作“中國的契訶夫”,意在把“西窗雨”與中國文學傳統融通起來,為如此獨特的自己做一份貼切的說明。
汪曾祺也喜歡蘇聯的安東諾夫、舒克申。這兩位作家善于描寫日常生活,排斥曲折復雜的情節,舒克申甚至說:“情節本身就帶有一種道德宣傳——這是無疑的。”他們就是契訶夫在蘇聯時代的余響。如何在蘇聯體制下激活契訶夫傳統,安東諾夫做出標準操作,他的操作也為“十七年”的汪曾祺提供了啟示。不妨把安東諾夫《在電車上》與汪曾祺“十七年”最負盛名的《羊舍一夕》做一個對讀。前者寫的是少年巴威爾坐深夜電車去上班,后者說的是四個孩子在夜晚的羊舍閑聊,他們俱在一種細碎但溫馨、有力、向上的生活流的披拂下“成長”著。幸福的“成長”總是家家相似:巴威爾透過寬敞的窗子看著城市閃爍的燈火,一會兒這家、一會兒那家,燈光陸續熄滅了,人們都睡了,那個不相識的姑娘大約也睡了,明天她也許還會坐這班車吧;四個孩子都睡了,燈滅了,從煤塊的縫隙里,透出隱隱的火光,小屋溢滿了薄薄的藹然的紅輝。契訶夫一定想不到,冰的自己也能與燙的時代化合,從而造就一種溫暖的美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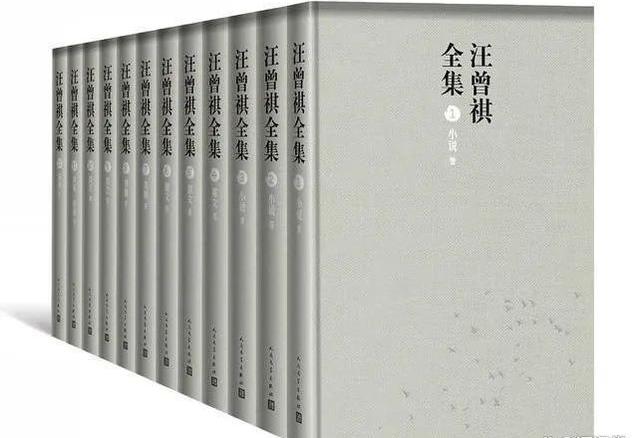
季紅真、劉偉等編:《汪曾祺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
奇異的是,那些讀熟了卻沒有能夠叩響汪曾祺的西方現代派文學,在他的精神世界里蟄伏、封存了數十年后,竟在他的“晚期”蘇醒、復活甚至噴發了。“晚期”汪曾祺尖銳、刻薄、大膽、憂傷,從心所欲而逾矩。比如,《小孃孃》那個亂倫的雨夜,“一個一個藍色的閃把屋里照亮,一切都照得很清楚。炸雷不斷,好像要把天和地劈碎”。這個場景、這些意象,分明來自波德萊爾的《情侶之死》:“薔薇色、神秘的藍色之夜/我們將互射唯一的電光/像一聲充滿離愁的嘆息。”也許,人就是會變的;也許,某些忘了的東西終究會復活,是忘不了的。
翟業軍
浙江大學文學院
310058
免責聲明:本號發布的圖文只為交流分享,源自網絡的圖片與文字內容,其版權歸原作者及網站所有,有疑問敬請聯系我們刪除!
減速器行業報告通過全方位調查分析和大量的客觀數據信息,對中國減速器行業發展趨勢、減速器價格及走勢、減速器競爭態勢、主要企業營銷情況等方面進行分析.
1900/1/1 0:00:00北京時間7月11日12時許,離岸人民幣兌美元收復7.20關口,日內漲超250點。 截至發稿,離岸人民幣兌美元暫報7.2067,漲225個基點,盤中一度漲近300個基點;在岸人民幣漲308個基點,
1900/1/1 0:00:00來源:證券時報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準確、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1900/1/1 0:00:00與奢侈品品牌FENDI聯名火出圈之后,喜茶又嘗試與珠寶品牌擦出新火花。7月10日,喜茶官宣和周大福聯名,以“喜提第一桶金”為宣傳語吸引用戶下單消費.
1900/1/1 0:00:007月12日,A股三大指數同步回落,盤面上超4200只個股下跌,智車產業鏈延續強勢,光伏板塊上行,AI全面大跌。截至收盤,上證指數跌0.78%,深證成指跌0.99%,創業板指跌0.9%.
1900/1/1 0:00:00一、投資邏輯 長邏輯1:低軌衛星呈美國領先、大國追趕的“一超多強”競爭格局以美國SpaceX為代表的頭部企業加速布局低軌衛星,軌道資源競爭白熱化.
1900/1/1 0:00:00